【人物專訪】劉學哲以「利他」精神,投入無障礙功能測試
文、圖/陳芸英
劉學哲目前在一家與Google合作的印度公司從事無障礙功能測試,工作地點位在板橋的Google園區,是公司的第一位視障員工。Google手機上市之前,是參與者也是中文的第一位使用者。
學哲是早產兒,從小一眼全盲,另一眼輕度視障。但小五的某天,午休起來突然發現視野只剩一半,考試成績驟降,父母帶去看醫師,才得知因早產導致視網膜剝離,僅存光覺。
他就讀於一般學校,由於看不見,國中起學習點字,運用盲用電腦輔具,吸收龐大的知識,不論靜宜大學和中正研究所,都讀資訊工程系、所。
但學校的知識並不能滿足求知慾強烈的他。主動參加與電腦和資訊相關的研習會或進修校外課程成了日常。像讀研究所階段,獨自從嘉義搭乘客運北上,克服萬難找不同的地方上資訊課,毅力驚人;尤其對新鮮事物非常感興趣,像AI剛出來時就開始自行研究,透過不斷摸索熟悉它們的功能與應用;同時思考該如何設計教學方式,讓學生能有效運用AI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學哲對如何搜尋資料有股難以言喻的狂熱。像朋友託買電熱毯,他會逛很多網站,比較細節,研究如何使用,判斷優缺點;連朋友去日本想參觀的景點和購買伴手禮他都當一回事,搜尋交通便利、價格便宜的住宿,還有好吃的零食;甚至視障者想考公職沒教材,即使自己沒有資料,卻願幫對方找。
學哲的休閒娛樂極少,與朋友互動都跟電腦有關。某日朋友問起帶他的站務員是男或女,沒想到竟忘了,還說,「頭腦本來就很聰明,會自動篩選重要或不重要的事。」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寫程式設計,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寫程式有成就感,如果一直跳出問題,我就會想辦法處理它。」
這份執著其來有自。有一次他想購買新的盲用輔具,原本期待輔具公司會為全盲消費族群設計無障礙介面,卻發現困難重重。因此期許自己能在資訊領域幫助更多視覺障礙者。他說,「身為全盲者,我比明眼人更加希望進步的網路科技能解決生活的不便。」
學哲的求職之路也朝資訊領域發展。但應徵時仍遇到多數視障者同樣的困擾。例如某公司誇讚他的程式寫得很棒,「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手寫的,」看似有機會錄取;然而進一步談薪資時,主管回,「我們內部先討論一下。」最後的答覆是,「你跟我們的team沒那麼適合……」或者當對方質疑他的視力時,還特地到該公司實際操作電腦,讓對方知道他的確有能力,依舊被打回票。類似的求職經驗屢見不鮮。初期難免心理受創,次數多了,只好自我安慰,「錄取當驚喜,沒錄取很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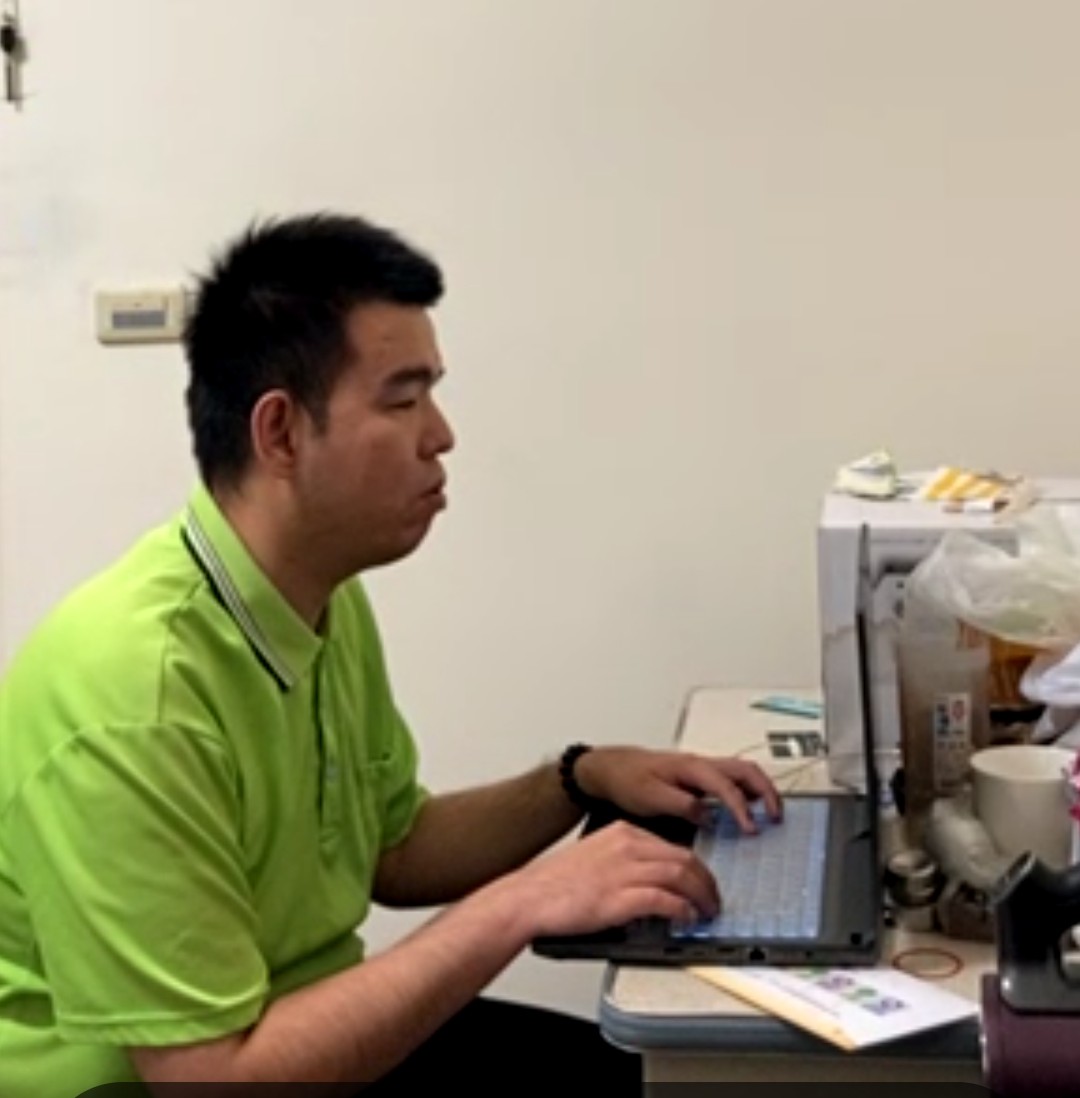
第一份工作是當年就讀靜宜大學時社團外聘的業界講師葉老師推薦的。篤信佛教的葉老師跟菩薩發願,一生立志幫助需要的人。大學期間學哲曾發生車禍,拆石膏後的一段復健,好幾次都是由住在新竹的葉老師排開工作,專程開車接送。「利他」兩個字在學哲心中萌芽。
葉老師得知台中惠明盲校缺人,問了學哲的意願。雖然程式設計是第一志願,但到學校當資訊教師或許是選項。「我覺得不管現在還是未來,特殊生提早接觸資訊也不錯。」實際上除了教電腦,還包括國中國語、數學……身兼多職。
教職兩年因約滿而離開。下一份工作則透過桃園勞動局引薦到健行科大電算中心擔任全端網頁開發人員,無縫接軌。
當時還處於疫情期間,訪客入校得用紙本填寫,主管問他可否做出QR Code,以手機掃描,省時又省心,他一口答應,「其實我沒把握,就當練習吧!」短短兩個月內,成功開發QR Code訪客登記系統,徹底改善低效舊有紙本登記流程,大幅節省訪客等候時間。完成任務,成就感油然而生。
話鋒一轉,他離開嚴肅的話題,談及一般人對於視覺障礙的刻板印象。原來學校另聘按摩師。某日下班聽到一聲,「師傅下班啦!」左顧右盼,沒有別人,「第一次被叫『師傅』,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才好!」
學哲喜歡健行科大的環境。同事熱情包容,工作愉快。但一年半後,得知Google的合作廠商——印度威普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印度公司)應徵台灣駐點的無障礙測試工程師。「比起學校,我覺得在業界能幫助更多使用者。」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視障者投履歷都自我設限於視障相關單位,學哲則往一般公司,連大廠都不放過,例如台積電。
這家印度公司是全球資訊技術、策略及設計諮詢和商務流程服務外包的引領者。
外商注重背景審查,例如確認工作經歷是否真實等。面試以遠端視訊,雙方開Google文件互動。印度公司的主管Raffa(台灣人)出三道題:一是閱讀,告知內容;二是拋出一個狀況,寫測試案例流程;三是以英文寫成報告,回覆給Google的工程師。畢竟Google的總部在美國。
這份工作為無障礙測試,幫Google抓出問題、手機更新之後是否符合規範,更以使用者的需求提出改進空間,確保用戶獲得最佳體驗,讓Google賣出的產品有品質保證。
Raffa明顯看出學哲技高一籌,不過錄取是幾天後的事。Raffa認為,既然提供輔助工具給障礙者使用,何不由障礙者負責;況且,障礙者就是使用者,最清楚「痛點」出在哪裡。
不過高層對全盲的工作者存有疑慮。Raffa事後打趣地說,「我寫了一篇『小論文』,克服萬難,舉例證明你的實力,才說服高層聘用你。」很巧,Google的其中一位主管就是視障者,所以視障者是否能勝任這份工作就無須贅述了。
工作一段時間後,台、美兩位視障者曾透過遠端視訊開會,學哲不全然聽懂對方說的內容,雙方僅以幾句簡單的英文交談;後來聽主管轉述,Google對學哲的評價頗高。
Raffa平易近人,對待同事像朋友般。某日跟學哲聊天時問,「在你之前,我面試的都是明眼人,但就速度一項,當他們還在思考時你已經寫完測試案例了。你是怎麼做到的?」
學哲認為極可能曾在惠明盲校教書的經驗有關。該校學生障礙類別多且障礙程度偏重,每一個步驟得拆解好幾個動作描述,並且從頭到尾講一遍才算完成,這與測試案例的步驟類似,例如發現某個元件有問題,就得把它一一拆解再放上去,讓工程師確認是否如此。惠明的教學經驗,的確增加他寫測試流程的速度。
Google手機是Android系統,但學哲使用iPhone。他比較兩者差異,「iPhone是站在障礙者的立場特別開一個無障礙專用道給你走;Android則希望視障者的操作模式更接近一般人,所以在道路旁設一條導盲磚。」
說來有趣,學哲就是覺得Android不方便才換iPhone,而多數同事也用iPhone。有人問他:「很久沒使用Android,在工作上會不會覺得蹩腳?」學哲說,兩個系統都熟,只是「手勢」不一樣而已。
手錶測試原本不是他的業務,但問及可否協助,學哲勉為其難地答應,而成果令Google主管很滿意。此後,很多別人做不好的事都落在他身上,業務量又加重了。
Raffa後來離職,但對學哲的評價始終如一。這份肯定對視障者有意義。這使得其他部門有勇氣再聘用視障者並且不再存疑,所以目前公司有兩位視障員工。
不過他坦言英文程度不好,以英文跟Google同事溝通是項挑戰。像是說服工程師解決一個很小的問題,就得思索如何寫才正確無誤。為了避免文法出錯,得先使用工具確認語法正確無誤,再正式傳給對方;而如何運用AI下指令,則考驗他的功力。
這份工作壓力大,真正開心的事不多。但「利他」精神一直支持著他。學哲懷抱著比別人多一點實力就可以為別人解決問題的態度,繼續做下去;如果同心協力解決問題,讓更多人使用無障礙環境,這才是值得開心的事。
